小息跨媒介創作室(簡稱「小息」)在《卡桑德拉/表象終結之世界》中的設計,結合戲劇與裝置藝術的元素,讓觀眾置身其中,體會劇作。劇本原創Kevin Rittberger提出了二重問題:從非洲走向歐洲的難民的處境如何?歐洲知識份子如何面對難民與自己的關係?第二個問題直指真正認識/經驗他人苦難及轉譯之不可能,那麼作品中的情感及意識的流動能否令觀眾有所共鳴便為關鍵,因為那是突破認知局限的契機。
Rittberger以田野調查的結果為基礎創作,但質疑寫實通俗的表達方式。他的文本結合多種表達形式,分別呈現了敍述上視點及聲音之差異性。《卡》的敍述層次複雜,除了從難民、援助者、海關、翻譯、紀錄片導演、作家等多個角度呈現難民的波折經歷,亦表達了從不同位置再現其他人經歷的限制,反身詰問關注/觀看別人困苦的倫理難題。簡單來說,是關懷者感到「好人難做」的道德焦慮,質疑自己的紀錄和轉達不夠真實、不夠設身處地,擔心自己有動機不純的優越感、恐怕越幫越忙或好心做壞事……劇中兩個歐洲記者代表了兩種取態:紀錄片導演Julika執著於消弭她和難民的距離,力圖擺脫偏見,親自乘上難民船,甚至不怕一起沉沒海底,越鑽越深,似乎最後只有毁滅;紀實作家Disk接受自身限制,認為人不能兼任紀錄者與救援者的角色,但他卻無法接受翻譯員表達上的偏差。

敍述的聲音也有複雜的層次差異,直接敍述、間接敍述和自由間接敍述的聲音隨時交錯;以其中一個尼日利亞難民Blessing為例,劇本開端對她的間接描寫、她的日記自述、戲中戲「教育劇」飾演Blessing的演員的台詞、她同行的丈夫Boubacar的轉述……等多個聲音交替。或者以「遇溺者的視點」為例,Julika在她與Disk的對話中說要拍Disk淹死、旁白描述Disk淹死、沙灘上的目擊者描述Disk淹死、Disk在水中的自白、Julika說自己可以和難民一起淹死、Boubacar轉述Julika淹死等多個敘事聲音也隨時轉換,所述內容是真實、虛構、記憶還是角色的想像也模糊不清。
「小息」的演繹以多媒體和空間轉移為手段,呈現出戲劇文本在視點和聲音上的差異性和複雜性。劇團在牛棚藝術村裡劃出多個演出區域,順著文本章節,讓觀眾不斷移動,從室外到室內,最後走進牛棚12號單位,沒有坐位,處於不斷流動、漸漸疲倦的狀態,指涉難民的漂泊境況。在視像和聲音的佈置上,觀眾在序幕先看到圍牆上海浪的大幅投影,演員以各種身姿處於當中。然後劇團領觀眾經過曲折狹窄的通道,途中會聽見不同人用外語說話的錄音,路旁放了一雙雙鞋子,感覺詭異;對照劇本,那些聲音和鞋子應該是不同人和物之簡述,但觀眾匆匆走過,而且聲音細碎,又是外語,不會聽到當中的內容。大概劇團的用意是,先後以視像和聲音配置營造出難民處境的氛圍,讓觀眾對主題產生初步印象,然後才對個別難民的故事作具體的描寫。
演出的下半部都在牛棚12號單位中進行,當中放置了多個顯像管電視機和幾個魚缸,在這裡即時攝錄和預先錄製的影像會在電視上顯示或投射在牆上。魚缸和電視機影像,呈現Julika所思考的「在水中」以及間接傳達的視點。最後電視屏幕上的蜘蛛網配合著Boubacar講述的有關蜘蛛的傳說,演出者亦以燈光提示觀眾留意四週牆上的粉筆字,表示觀眾猶如在船艙之中,與劇作中兩類人 — — 非洲難民和歐洲知識份子 — — 的經歷連繫起來,亦承接了序幕大海的環境意象。除了作品中作為批判對象的「教育劇」一部分,「小息」的聲畫裝置和空間移動的策略使觀眾置身於劇場作品中,而非在一個抽離的位置觀看舞台上的事件。換言之,《卡》藉著Julika提出的「關懷他者之倫理」和「對別人處境之再現」等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,「小息」仍然試著回應 — — 當然了,否則這些香港的藝術家怎會翻譯/演繹一個德國劇作家講歐洲知識份子和非洲難民的文本?

「小息」的創作心思值得肯定,而從觀眾的角度看,演出效果如何呢?
首先,Rittberger的敍事形式夾雜著多種風格,包括了以日常語言呈現通俗情節的部分,也有敍事角度遊移不明、虛實難分、詩意的意識流描寫,也就是說,他以難以轉達的語言風格來講述「難以傳達」這主題,難上加難。「教育劇」的部分是通俗易懂的,卻也是被批判的,而「小息」邀請了一些觀眾即場飾演「教育劇的觀眾」角色,讀出相應對白,置其於某個非洲人的位置,質疑這種敍事語言和歐洲人潛藏的排外政治議程有關--因為通俗的表達手法和注意力聚焦於舞台的演出正是政治宣傳(Propaganda)所需要的。但是香港觀眾要代入對「教育劇」不以為然的非洲觀眾的處境,則需要多一點引導,否則抽離的批判性恐怕會被即興參與的遊戲性取代。
在12號單位演出的下半部,當幾位演出者交替演繹文本中多個角色直接和間接敍述的內容時,正如上文所述觀眾們被安排在一個「身歷其境」的狀態中,演員們的肢體動作、敍事聲音、即時攝錄的電視錄像在觀眾們周遭發生,注意力分散。雖然說這安排讓各觀眾自行調校焦點,也可說他們不斷被干擾以致分神,加上原文本「富有挑戰性」的語言風格,可能便觀眾能量渙散,如在波濤中浮沉掙扎,不利於他們體會劇本和演繹者在細節上花的心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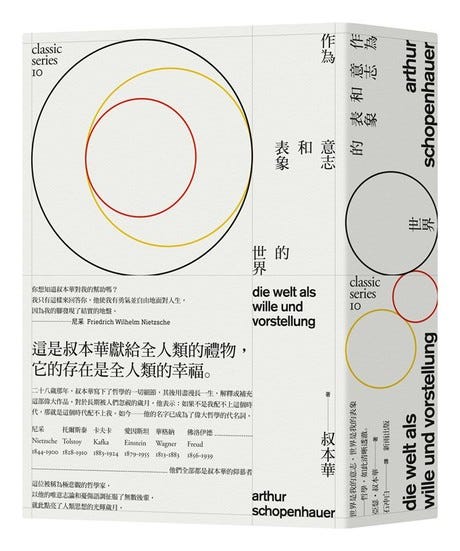
敍事層次複雜細膩正是《卡桑德拉/表象終結之世界》的特色,但Rittberger以哲學家叔本華的《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》為參照,最後以非人類的視點 — — 溺死者、「水底精靈」和珊瑚 — — 在大海中融為一體的意象作結。世界表象繁多,終同歸於世界本體的意志。難民們為了生存和發展,不惜冒生命危險渡向歐洲,其求生的慾望和痛苦的掙扎就是那接通萬物眾生的意志,使Julika那大概是發達國家的知識份子才會有的煩惱未免顯得庸人自擾 — — 直至人涉入「海底亡者的觀點」這麼徹底的、非人的境地。
那麼(在Boubacar轉述中)Julika把攝影機丟進海裡、再跳海自殺的行徑,若非瘋狂,就是悟道。那看來是反藝術的,那麼《卡》這作品是自我抵消的嗎?但在叔本華的痛苦意志之外,這作品的另一參照是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(Cassandra),一個注定預言不被相信的先知。雖然翻譯和再現似乎總是誤解和偏見,就如卡桑德拉那宿命的警告一般,Rittberger仍在序章中提出一絲改變的希望,「把夢翻譯成另一個夢」而非悲慘現實的希望,那讓難民們前仆後繼、九死一生仍要冒險的希望。
對叔本華來說,表象指向認知和經驗上的限制,但藝術是意志本體之模型,也是「另一個夢」的翻譯工作,傳達的最重要是情感而非知識,可為人帶來痛苦中的慰藉。可惜「小息」讓觀眾置身其中的配置也使能量易於分散,加上文本艱澀之處不少,要引起共鳴更不容易。
[原載於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(香港分會)網站;2018年4月6日]
演出資料:
主辦︰小息跨媒介創作室
地點︰牛棚藝術村
日期︰30/1/2018
